沉家桢:学佛经过
发布时间:2024-06-10 01:18:44作者:心经问答网
各位法师、各位同修。今天张鸿洋居士叫我向各位报告我的学佛经过,以 供各位考。实则我所能讲而值得供各位参考的极有限。这几天来各位已听了很 多法师大德的佛法开示,我衷心期望各位已很法喜充满。我的这一点点报告, 只能说是大餐后用点点心,能助些消化,已经很不错了,希望各位不要见笑。
昨晚想想学佛的经过,发觉有一点值得向各位提出报告:我现在的心态, 是衷心感激这一生中,所有遇到过的法师、长者、大德、善知识、父母妻友。 而特别要强调,我昨晚所发觉的一点,是我衷心感激所有见到过的男人女人, 不论时间短长,即使仅是见过一面,笑过一笑,说过一句话,批评,赞叹,都 对我的学佛,是有影响。甚至于不仅是人,一切有情,一猫一犬,只要有缘遇 到,都和学佛有关。甚至于无情的众生,也不例外!
我举一个例。几年前,香港来了一位法师,我很惭愧,此刻连他的法名都 想不起来。他送了我一串十八粒的黑色念佛珠。以后既没有通讯,也没再见面 。可是,各位,我那时怎会想到,这黑色的宝石念珠,竟会是今天各位面对着 的千年古观音的眼珠!
回忆我的学佛经过,我得报告:我母亲是极虔诚的观世音菩萨的信仰者。 我的对观世音菩萨的恭敬信仰,可以说是渊源于我母亲。而在中年以前,凡遇 到急难的时候,总是祈求观世音菩萨,也是得之母亲一直的熏导。
我到现在为止,佛经中缘最深的,一是楞严经,一是金刚经。楞严经是我 第一本看到的佛经,也是我对佛法发生兴趣的开源。而这本佛经,则是我无意 中在父亲的书架中抽到。我常想假定父亲不买佛经,不放在书架上,我什么时 候才会有缘接触佛法呢?即此一事,我已应十分感激我的父亲。
一个人年纪大了,回忆起许多过去的事实,有时真觉得不可思议!十七岁 的时候,我曾经有过一个梦,因为讲过几次,至今还显得十分生动。而这个梦 ,经过六十多年的事实证明,简直像是我的自传的缩影。
那是一九三零年,我梦见我在挤满了人的一个大圆顶的广厅中。这大批人 中,最令人注目的是许多小孩子都结了红色的领带。各位,那时候根本没有后 来所谓红卫兵的观念,也没有在任何书本照片中看到过这种红领带的孩子。在 梦中,有人对我讲,这个地方正在革命,你得赶快离开。
这个大厅有三道门,梦中觉得都有人守着,但终于冲出了这三道门。外面 是一条小河,我就躲到河边很高密的芦苇中。远远的看见有四个背掮着枪在追 寻我的人。
隔了一段时候,我走出芦苇,听见河的那岸有人在叫我。那是一位中年的 女士。她左臂挽着一个竹篮,篮里有一团淡黄色的绒线,她正在织绒线。各位 ,请记住这一点,因为下面我还会提到。
当我看到她的时候,心中生起无法形容的舒适感受。她那慈悲、祥和、微 笑的脸,竟令我舍不得将眼移开。
「你为什么要在那边呢?我这边要好得多哩!」十分柔和的声音。
「我怎么过河呢?」因为我觉得这河太宽,没法跳过去。既不见有桥,左 右也不见有船。忽然,我觉得这位女士即是我母亲常讲的观世音菩萨!
「你看!」我跟着她指的方向,看到河中涌出一连串的木桩,可以踏着过 河。
当我踏着木桩过河时,看到有许多鸭子在混浊的河水中,以各种姿态戏水 。忽然,这许多鸭子都变了裸体的婴孩,也一样的以各种姿态在游泳玩耍!我 急急过河,也没有功夫去顾到这些婴孩。可是鸭子变成婴儿的这一个念头,始 终忘不了。这个梦之后,我对鸭子就觉得吃不下口,一直没有再吃。
这时候我已经站在那女士的面前。她指着一个方向,很关心的对我说:「 你看!那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!」
那是一望无际一片黄金色的麦田,麦浪起伏,远远的地平线上,太阳正放 射着万道金光。这是一幅永不能忘怀的景色!
我是生长在杭州。小学、初中是在英国人主办的教会学校念书。我们得读 圣经,得做礼拜。我们有一位很好的教科学的老师。有一天他带了一个彩色的 眼睛模型来上课。他很生动地讲解了人眼的结构、功能、效力。最后,他说: 「现在你们可以明白,眼睛只是一种工具!工具用得久了,或者用得不小心, 它会旧、会破、会坏。正如我们的眼睛也会老,会有病,看的能力会逐渐减退 !」
在听老师讲这个结论的时候,忽然心中闪起一个问题:「如果眼睛只是一 种工具,那么谁是使用这工具的主人呢?」
在我读的教会学校里,有一位训导长,他也是牧师。学生有什么问题,都 可以去请教他。他是一位很慈祥的老师。所以我就将我心中的问题去请教他。
他听了之后,很安祥的对我说:「孩子啊!上帝造了您,给您眼睛,当然 您是主人翁。还有什么人是用您的眼睛的主人呢!」
「慈父啊!(我们都称他为 father )可是我又是什么呢?」
他没有正面的答复我这个问题,只叫我好好的去多念圣经。可是我在圣经 中找不到答案!
各位!昨晚我整理一下我的学佛经过,觉得应该以父母的缘,十七岁的梦 ,及眼睛只是一种工具的这个发现,作为我学佛的第一阶段。而在这阶段中, 「用这工具的主人翁是谁呀?」这个疑问,现在想想,实在是学佛的核心。希 望各位能放在心中,也许即是这一句话,可以启发您本具的智能。
本师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:智能人人本具,本来圆满。所以既不是可以 求得,也不是任何人能够给您,要靠您自己启发。而您遇到的任何人,遇到的 任何事,不论这个人、这件事,以您的心态认为是好是坏,都有可能启发您本 具的智能。这种机会,要看您是否抓得住。
我回忆学佛经过的第二阶段,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动荡的一个阶段。从 高中、大学、订婚、抗战、被派去德国、世界大战爆发,一九四一年回国,结 婚、去昆明参加创办电话制造厂。一九四五年,抗战结束,回到上海,创办私 人企业;然后一家六口(这时又添了传缙及馥儿)迁香港,往伦敦,一直到一 九五一年定居美国。这其间千变万化,艰苦惊恐,举不胜举。但现在想想,「 用工具的主人翁是谁?」这个问题,却一直随着我的生活,在滋长扩大。
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,我已深信不但眼睛是工具,五官四肢,内脏头脑, 这整个肉体,事实上没有一件不是工具。换句话说,父母所生的所谓我,只是 给我的一套工具。这套工具,生下来的时候,就有好有差,会旧会老,要有病 痛,在一刻不停的变,终至于会死亡消灭。楞严经中佛称之为「攀缘心」。而 称真真的我为「识精元明」「能生诸缘」「元清净体」。但在这第二阶段,我 对这文字上解释的真我,都还不够清楚,更不必谈有什么实证了!
在这千变万化的二十几年中,有三件事值得向各位报告。也许因缘偶合, 有的会引您生起一些启发。
第一件是有关我这生学佛过程中遇到的重要人物居和如。和如的姊姊和我 姊夫的三弟孙祥萌是夫妻,他们都住在上海。从未见过面。我去上海进交通大 学的时候,曾因祥萌兄嫂的介绍,和和如见过二面,都是十分匆促,并没有谈 过话。知道她父亲是中国银行总行的副经理,家教很严。
当我进入交大二年级的时候,被选为级长。有一次,我已安排了在星期六 下午召开执行委员会。星期四的那天,当我从图书馆做了功课回到宿舍时,同 学对我讲:「有一位居小姐已经来过三次电话,要请你回她电话。」将号码给 了我。我一时还想不起居小姐是那一位,根本没想到她会打电话给我。
「这个星期六下午你愿不愿同我到大光明电影院看个电影?我们二点钟在 那边会面。」电话接通之后,一种轻松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我心中立刻想到我有执行委员会开会啊!可是嘴竟不听我心(攀缘心)的 指挥,说:「好啊!我们下午二时在大光明电影院会面。」
一见面,她就开口:「我最近织了一件绒线背心,想送给你,不晓得大小 对不对?」那是一件淡黄色的绒线背心。突然,十七岁梦中观世音菩萨在织绒 线的那个镜头,在心中一闪。以后的发展,各位也许已猜想得到。她和我在这 世上圆满了五十年夫妻同修的缘。
第二件事发生在德国柏林的地下防空室中。
大学毕业后,我参加了资源委员会。一九三八年初,政府派我去德国,和 原在求学的三位工程师共同筹备在中国兴建电话机制造厂。而我担任了和合作 厂家西门子的连络人及负责采购必需的机器及工具。
在出国之前,我原想和居和如结了婚一同去德国,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。
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,柏林全市居民都发给了粮食券,高楼上也架起 高射炮,情况看得出十分紧张。九月一日,德军入侵波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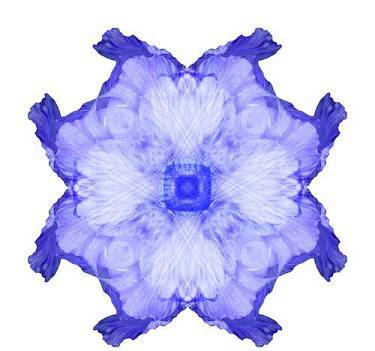
我收到政府的一个急电,训令我自己决定今后行动。我考虑再三:留在战 地有生命危险,又急想和和如早日结婚。可是电话厂的机器设备,虽已完全订 购,但仅极少数交货起运;设计图样,也仅一小部份已由西门子交来。此时我 若离开,不但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;抗战祖国的急需通讯设备,更将受到无可 补救的缺乏。我不能走!
这天下午,我和那三位工程师在柏林中央火车站握别,一股强烈的凄凉孤 独的感觉,笼罩了我全身。
回到西门子招待所,已晚上八时左右。一进卧室,即倒在床上,可是不能 入眠。正似入睡时,又忽被尖锐的空袭警报声惊醒。匆匆的抓了一张毡子,走 向指定的防空地下室。一到门口,可把我惊住了。所有已在防空室中的人,都 已戴上了防毒面具,只有我没有!
我勉强挤到离门最远的屋角上坐了下来,觉得有很多人的眼睛都看着我。 心中这时很明了,倘若毒气来袭,我将是唯一的死亡者。各位,一个人在面临 生死绝望的关头,脑筋会特别敏锐,幼年时母亲对我讲的话,都记了起来,我 赶紧念观世音菩萨。突然已好多年不想的一个问题,涌上心头,「谁是用这工 具的主人翁呀?」毒气可以使这套工具失其效用,可是用这套工具的主人翁呢 ?我又想起楞严经中佛不是说攀缘心是有生有灭,而本清净体则是一直来恒久 不变,没有生死。那么,究竟谁是用这套工具的主人翁呢?还是攀缘心及本清 净体都能用这套工具?我忽然又想起,为什么那天居和如打电话约我去看电影 时,我心中在想:「不可以呀!我有执行会议呀!」而嘴里却说:「好啊!我 们在电影院见面。」我正在沈入深思的时候,忽然觉得防空室中的人都在走动 了,原来已是警报解除。走出室外,秋风一阵吹来,将我的沉思吹得烟消云散 ,依然故我,仍在柏林!
一九四一年春在德国任务已完,回到上海,结了婚,取道越南,到了昆明 ,参加创办电话制造厂。在中央电工厂的总经理恽震,第三厂(即电话厂)厂 长黄君可领导之下,真是一草一木,点点滴滴,都是重新做起,日夜忙碌。小 夫妻一对,克勤克俭,既没有假期周末,又得常跑日本飞机来轰炸的警报。我 们住的一所小屋,曾一度中弹,全部被毁(包括和如送我的淡黄色绒线背心) ,所留下的,说来奇怪,只有挂在墙上的一张结婚照片,连玻璃面都没有碎( 现在还挂在我的卧室里)。这样忙碌的生活,一直到抗战结束,一家四口(那 时已添了二个女儿,梅儿、蕙儿),回到上海。
第三件事发生在上海的浴室中。
上海虽是一个大都市,但那时候还很少整个住宅装有热气设备的。一天, 我去浴室洗澡,室内已先放了一盆烧红的炭。不知何故,我这次去洗澡,竟会 忘了将浴室的门锁住。这间浴室在洗脸盆旁边有一扇小窗,当时也关着。
进去的时候并不觉得怎样。可是,正要踏进浴盆的时候,忽然失去了知觉 (显是中了一氧化碳的毒)。可是奇怪的是我还能转过身来将小窗推开了一些 ,并且扶住洗脸盆,面对着镜子,而不跌倒。又竟慢慢的醒了过来。
后来家人对我讲:梅儿在浴室门口,说爸爸在做怪脸,又在用手拍腿。
我回忆分析这件事的经过:是梅儿正好此时走过浴室门口,无意中推开了 一些浴门,我在失了知觉后又去推开了一些小窗,因此得有少数清鲜空气的流 动,使我稍稍回复了一些知觉。因为在竭力念观世音菩萨求救,可是没能念出 声音,只是嘴动及脸部的表情,所以梅儿说我在做怪脸;也因为我在想用手拍 后脑以刺激神经,可是手提不起来,所以梅儿说爸爸在拍腿。
当时我看见镜子中有一个一尺多高的小人,欲进又退。心中在急:「这个 小人就是我!不能让他离开呀!他走了,我就死了!」
这样进退了至少三次,终于走了前来。小人一消失,我已恢复了知觉,赶 紧将门推开,梅儿那时已不在门外。
各位,这件事对我的学佛有相当影响。
使我亲身体会到,人命随时可以终了,也即是这套工具随时可以破坏,真 是差不得一点。
什么人在想这个小人就是我?如果小人是我,那么在想的就不应该是我。 究竟楞严经中佛说的攀缘心及本清净体的区别在那里?
是什么力量使我失了知觉之后,还能转身去推窗,还能晓得要扶住洗脸盆 ,而不倒在炭盆上?
这一阶段,现在回忆起来,应该称为我学佛的退转阶段,也说明我学佛基 础的浮浅。在那一段时间中,既没有念经,也没有拜佛。令我想起那十七岁梦 中的冲出三道关门!
在这第二阶段中,有二位善知识,我必须提出:一是第一次遇到我学佛过 程中的第二位重要人物──张澄基。他那时在印度。我从昆明去印度时,特去 拜望他。他那时给我的深刻印象,是后来在美国再遇见他时所以会全心全意跟 他学习佛法的主因。二是在香港认识了月溪法师,他是我第一位接近的中国法 师。从他那里,我听到了不少「空性无限」「真空妙有」的佛理,也懂得了一 些参禅的法门。但对于我原有的疑问,似乎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启发。
初到美国,物质及精神上的生活,都很艰苦。我英语差得太远,常和美国 人讲话时,看见对方眉头一绉,心里就生起惭愧难过的反应;风俗人情,又十 分生疏。所以在贸易公司解散后,一度失业彷徨的期间,眼看着和如带着四个 小孩(我们一直没有佣人),真是心疲力竭,耐苦耐劳,那种同心协力的热情 ,暗中常令我尝到酸痛爱怜的滋味!
那时,给我助力最多的是贸易公司纽约分公司经理陈棨元及魏重庆和原本 是贸易公司的律师 H. L. White。一直到进入航运,向美国政府买到战后剩余 物资的油轮,开始为台湾运从波斯湾至高雄的原油,生活方才安定下来。
五个星期住在纽约市的旅舍中,没有一次回家,同陈棨元、Mr. White,日 日夜夜,和土耳其政府代表团,谈判接洽为土耳其购买及定造十五艘船只。及 至这件业务达成,方才透了一口气,也奠定了我的航业基础。
我学佛过程的第三阶段,形式上要到一九六二年方才真真开始。可是我为 什么跟各位叙述这一番在美创业艰苦的经过呢?因为这两者实在是息息相关, 没有这一番艰苦,也不可能反映出日后张澄基让我在佛法中启发出本性的清净 。
正是中国诗人所说的:
不经一番寒澈骨 那得梅花扑鼻香
在这一阶段中,对我学佛最有影响的是二件事,也是二个人。这两位,现 在都不在了!您说是观音使者,或者是善知识,都可以。总之,对我的学佛, 影响很大。
第一件事,是一九六四年,我和棨元兄等经营的公司第一次决定发给红利 。那时候对我们讲,是一笔很大的金额。
那天正好是我和和如结婚的二十三周年。我从公司回去,告诉她将有这笔 收入时,两人都很高兴,小夫妻商量应该怎样去善用这笔钱。
我和和如都是受过基督教会学校的教育。她那时还没有表示对佛法有兴趣 。而我则已认识了乐渡法师、张澄基、陈健民等一般佛教人士。平时当她和我 讨论宗教信仰时,她常说:「您们啊!老是咬文嚼字,只会讲不会做。基督教 虽然道理讲得不多但是办医院、办学校、孤儿院、老人院,做许多人们很需要 的事。为什么佛教不做点这类的事呢?」我那时已稍稍懂得一点佛法,总劝她 :「办医院、老人院、孤儿院这种的确都是好的,这种是所谓修人天福报。下 世也许可以升天,也许更富更贵。但仍免不了堕落的可能,还是在六道之中。 所以学佛,一定要修慧,那方是究竟解脱的正路。」
那天我们商量怎样运用这笔钱时,也涉及了宗教信仰。她还是主张修福, 我还是主张修慧。可是她很聪明,她说:「好吧!修福、修慧既然都是好的, 那末让我们来分工合作。您去修慧。您有了智能,将来可以将佛法讲给我听。 我来修福,福报好,至少可以烧饭给您吃。」我记起佛教中有一个「罗汉托空 钵」的故事。觉得她的话也很有道理。于是决定将那笔钱一分为二,每人一半 。她的由她作主修福,我的用来修慧。
在这以前,我已因和如的朋友姜大嫂认识了初来美弘法的乐渡法师,已参 加了他所领导的美国佛教会。佛教会在纽约市北区租了一处公寓房子,办了一 个佛堂,她很少去。但自从那天分工后,她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做义工帮忙, 烧饭洗扫,一切都做。我看在眼里,心中很觉得高兴。
大概在收到公司的钱不满二个月,有一个星期日,和如和我从美佛会出来 ,预备走到停车场去,忽然看见广告,有一座门面相当大的房子出售,原本是 电话公司的办公厅。和如叫我将电话号码抄下来。
我不明白她的意思。她说:「我们不妨约个时间来看看,也许可以买下来 给美佛会做寺址用。」
「那里来的钱呢?」
「用修福的钱啊!」
「您不是说应该办医院、办学校、老人院、孤儿院吗?」
「这一点点钱,那里够办这类大规模的善事呢?美佛会现在的地方实在太 小了!何况乐渡法师说,有三尊大佛像在香港定做,不久将运来。我们需要这 么一个地方,可以多容纳一些人,使他们来了解佛法。」她还加了一句:「也 使您可以有地方多修一点慧。」
这个电话公司的办公厅,就是现在的大觉寺。
所以和如修福修得很快,而我的修慧呢,可不容易,惭愧得很,一直到一 九六九年,五年之后,方第一次在大觉寺用英语讲五眼 Five Eyes 。
第二件事是在我们的船公司正发展得轰轰烈烈,我事务繁忙的时候。张澄 基(他那时已在宾州州立大学教佛学)说服我,跟他去在二所大学的修静场所 教我佛法。一共三次,每次三个星期。和如也很鼓励我,支持我去。
我们得早上四点起身,我不准说话,可以用笔问问题。他说,他没有资格 传法,但已经得到他师父贡噶喇嘛(那时已圆寂)的允许,代他传授,所以可 以将所有他在西藏、西康学到的密宗法门讲给我听。他也教我中国的禅宗修法 。
我得承认,这种机缘,也可以说是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可是我资质太差,有 时听了似懂非懂,有时也容易忘记。每次学习回家,又不能依照习练,但我对 于澄基兄的恩缘,永志不忘。他是我这生学佛过程中第二位影响最大的人!
当第三次完结的那天,他说:「您今天不必打坐,也不必念咒,要一念不 生,在山中盲目的经行(即是走),不要认方向,不要想走到什么地方去,也 不要担心迷路。下午再见。」
等我忽然再看到修静的那个场所时,大概已经是下午四时。走进厅内,看 张澄基坐在那里,我也不去理会他,一直走到自己住的房间,在打坐的地方坐 了下来。面前的矮桌上放着一部大般涅盘经。可能是我走了一天,已头昏目晕 ,觉得书上在那儿放光。忽然我注意到窗外在飘白雪(那时是四月),心中闪 了一个念头──是贡噶师父来了。这时方才看到张澄基就站在我边上,向着我 微笑。
各位,一直到后来,我方才听人讲,贡噶的西藏文意义即是白雪!
第二天一早,我仍不讲话,收拾了行李,下山去小铺子中吃早点,侍女给 我看菜单,问我要点什么,我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,还是一句话也不会讲,侍 女以为我是哑巴。
那天我开车,在纽约州的高速公路上开,心中好象还是一个念头都没有。 张澄基坐在旁边,看着我说:「喂!家桢,开车得当心一点。」
「打三百棒」我对他一喝。
「打三百棒」他回了我一句。这一下,可将我打醒了,我就全副精神的慢 慢开车回来。
一九六九年,船公司的总经理 Mr. White 忽然中风去世。我和棨元商量, 决定将船公司出售。
一九七零年出卖成功,在经济上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。但使我最高兴的, 还是那天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和如时,她对我讲:「我们现在不要一个修慧, 一个修福了,我们应该通力合作,两个人一起来福慧双修。」
庄严寺即是在这个「福慧双修」的原则下,推动出来。这一阶段,我修慧 的代表作,应该是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大学所讲的「观世音菩萨的证悟过程及 修行方法」。
我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,我学佛的第四阶段,尚未终了。第四阶段是从一 九八八年七月三日晚和如往生、八月四日一早我去佛堂发愿继续替她念金刚经 开始,负责庄严寺大佛殿的建造、千年古观音的降临、写【金刚经的研究】, 及电子佛典的推动,都是这阶段中的重要梦境,我还没有看到地平线上太阳放 射着万道金光。十八岁时,曾在故乡绍兴,一个小山上的观音庙中,抽到一支签。那是我第一次在寺庙中见到慈容满面的观世音菩萨像。现在将这支签记在 下面,祝各位身心愉快!
高危安可涉 平坦自延年
守道当逢泰 风云不偶然



